一
丫头,老了。
靠着一把木椅,一坐就是一个下午,对着远山的方向。
身旁有猫,有狗,还有顺着竹竿攀爬的丝瓜藤,绿色的藤架上,缀着几朵黄色的小花。

丫头的头发花白,不见了曾经乌黑的辫子,也不见了曾经圆圆的酒窝。当然,丫头也不能叫做丫头了,已经变成老太太,就跟小伙儿一样,已经成为了老头儿。
还是叫做丫头吧,在几千年的宁厂面前,丫头,永远是丫头。
子女都已经搬迁到县城居住,老伴也已经去世多年,就葬在对面的山腰。丫头只愿住在古镇上,每天坐在曾经和爷爷一起经营过的饭店门口,看着木板上的蜘蛛挂着丝线,一甩一甩。
丝线若隐若现,亦断亦连。
就跟这宁厂的历史一样,看似千丝万缕,却始终脉络清晰。
也如这纵横交错的盐道一样,看似断瓦残垣,却始终紧密相连。
最后,得说说这绵延几千年盐巫文化背后隐藏的神秘和无限的延续了。
前面已经说了太多盐巫文化的辉煌,这是史诗般的感动与厚重,这是文明的发源和延绵。
可终归,盐灶熄灭了,盐道在消失,房屋烟囱在垮塌,这样的垮塌却让宁厂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在崛起。
物质层面的消亡成就了精神层面的升华。
所以在前面,进行了太多了引述、假设或论证,包括把这条盐道上升到文明大通道的高度进行膜拜。
但膜拜不是盲目的,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,是建立在打破常规之上的论断,是尊重事实之后的严谨,是对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。
所以,这潺潺盐泉,绵绵盐道,带给我们的是无尽思考。
思考,还是继续从宁厂开始吧。
源自宁厂,又高于宁厂。
宁厂是安静的,安静的地方,适合思考。
宁厂又是喧哗的,喧哗的时候,更需要思考。
在盐泉前的后溪河边,觅一块光滑的石头,坐下,继续思考一些话题。
首先要说说巫溪和巫山两地共同拥有巫文化发源地这一至高的荣誉。
全国2000多个县级城市,以“巫”命名的只有巫溪和巫山,足见两个县的渊源,两个县的缘分。
这种缘分,是从上古时的巫咸国开始的,是从夏商周的鱼邑巫郡开始的,是从“秦立巫县”开始的。那一年是公元前227年,秦昭襄王取楚之巫郡归于黔中郡,设立巫县,县域包括现在的巫溪和巫山。秦统一六国后,推行郡县制,巫溪属南郡巫县。东汉建安十五年(210年),巫溪从巫县分出,单设为北井县。隋开皇三年(583年),置建平郡,巫县更名为巫山县。以后的各个朝代,行政管理方式各有不同,巫溪巫山两地也分分合合,分属过不同的行政管辖。
这个过程已经说了很多,再次提起,是因为如今到两地的外地人,经常把巫溪叫成巫山,也经常把巫山叫成巫溪。其实,叫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们都姓“巫”,行政区划分不开几千年的情缘。
山为阳,溪为水,水为阴,阴阳合一,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。
这是巫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,敬天敬地敬万物的文化内涵中,对立是表,融合是本。
巫溪、巫山,怎能分开?
不能分开的,是山与水的相互依赖,是山与水的相互信任,是山与水的情投意合。
不能分开的,是阴与阳的对立统一,是阴与阳的相互依存,是阴与阳的和谐交融。
这种缘分,是要感谢以巫咸为代表的十大巫师们的,他们创造了“万物有灵”和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的巫文化,创造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母体文化,才有了几千年的亘古不变。
一座宝源山,一池盐泉水,流进了大宁河,汇入了长江。
巫溪,巫山,山水之中,生生不息。
面对这种亘古不变,又不得不引来第二个问题:巫文化既然是母态文化,为何如今却被世俗眼光看成封建迷信的表现?
有关巫文化的演变过程,在《盐巫神秘》的章节里已经作过详细阐述,这里只简单梳理一下。
早前的时候,巫是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人,比如巫咸,既是大巫师,又是部落首领;比如屈原,做过楚官,兼管内政外交大事,有研究指出他就是一位巫师。到春秋诸子百家时期,普通人依然还相信上古人神不分的传说记载。比如,传说“黄帝四面”就是典型的人神合体的巫文化理论,今天的黄帝陵也是按这个说法设计的塑像。孔子时代的人都觉得黄帝是半人半神的形象,但在《论语》中孔子却将神话中的“黄帝四面”解释为“黄帝派遣了四个大臣分制四方。孔子删定典籍,建构儒家思想教材;汉武帝废黜百家,独尊儒学,使《春秋公羊学》成为最通显的儒学说。

汉代,成为巫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分变时期。
自此之后,原始巫文化名存实亡,巫术日渐走邪,巫也向多方向分解。封建王朝时期,许多宫廷政变中掺杂了巫术的痕迹,于是统治阶级更开始“谈巫色变”。
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今天,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,人类早期文化中无法解释的许多现象都得到了科学的阐述,巫文化中的部分“巫术”更失去了生存空间。
其实,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总是在变化中发展,又在发展中变化;同时任何文化里面都是既有精华又存有糟粕,文化本身并无“好”与“坏”之分,而在于使用者如何理解和运用。
特别是巫文化作为一种幼年文化、母态文化和人类懵懂时期的起源文化,有它至高无上的荣耀,也不可避免有着各种局限。科学的文化观,是不能过度拔高,也不能肆意打压。去伪存真,摈弃糟粕,留存真谛,同样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。
时至今日来研究巫文化,就是要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梳理,梳理出它的精华,记住它曾经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。
这种震撼,是几千年辉煌的延续。
这种感动,是几千年文明的力量。
当然,带给我们这种震撼和感动的,不仅仅是巫文化。在三峡,在中国版图的腹心地带,研究巫文化,是必须和盐文化一起的。
接着得说说第三个话题了,也就是关于“盐”和“巫”关系的问题。
还是继续重复一下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《说盐》里的三个观点:
一是产盐的地区,或食盐供应方便的地区,便是人类乐于聚居的地区;二是食盐是最早推动商业发展的商品;三是人类文化,总是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。
在苍茫盐道,在三峡,在宁厂宝源山,用几千年的传承印证了任先生的观点;有了先生的观点,一切辉煌和神奇又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。
从几亿年前的地壳运动开始,到三峡隆起从海洋变成陆地,再到第一泉盐水被人类发现利用,到巫咸古国、唐宋盐都、明清辉煌,一直到1996年腊月二十九日最后一灶炉火的熄灭,盐,成为贯穿这一地区的始终。
与盐一样,被人类一直使用传承的,还有巫文化。
一个物质层面,一个精神层面,就这样伴随了巫巴山地民众几千年之久。
盐,因为巫而被赋予更深的内涵。
巫,因为盐而被更加广泛地传播。
“盐”和“巫”,互相依赖着对方,又互相成就着对方。
这盐,是宝源山的盐,也是整个三峡的盐;这巫,是巫咸国走出来的巫,也是三峡走出来的巫。
学术研究,既不能狭隘,也不能自大。
巫盐,不是狭隘地仅仅讲巫溪宝源山的盐,而是代表整个三峡诸盐,更代表“巫”和“盐”,精神和物质共存的文化。
还得说说关于文物佐证的问题。
说了宁厂太多好话,但很多资料都缺乏更详实的文物佐证,毕竟,对历史文化的论证除了依据典籍记载之外,还需要历史文物。
缺乏历史文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:
一是宁厂特殊的地理位置,两岸山势陡峭,山洪水异常迅猛,呼啸而来,房屋尽毁。
《巫溪县志》和《巫溪县盐厂志》里有这样的记录。
清嘉庆六年(1801):盐场大水,冲没100余盐灶和不少民房、铺户。
清嘉庆八年(1803):盐场大水,全镇被淹;因是夜雨,河水陡涨,居民未及防患,房屋被水冲走,淹死男女417人。
清道光元年(1821):六月,大水淹没县署头门石阶7级。
清道光十三年(1833):大旱,绝种粮,人相食。
清咸丰八年(1858):八月,久雨,猫儿滩山陷,死亡1000余人,河道断航。
清同治六年(1867):夏,阴雨兼旬,溪水陡涨10余长,羊桥坝水淹月余,谷尽腐烂;宁厂冲去盐灶、居民90余家,死人亦多。
清同治八年(1869):七月,大水冲毁宁厂龙君庙、县城北门城楼和城垣200余丈。
清光绪四年(1878):六月河水大涨,冲走灶房十余家,燃料、衣物、器具无数,道路受损严重,商家无钱周转致生产停顿。
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):秋雨48天,次年奇荒,知县熊芙菁以工代赈修筑城墙。
100年时间,载入志书的大灾就达到9次之多。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时间,乃至到先秦时代,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就更差,一切,都随着滚滚洪水而去。
大宁河,馈赠了两岸子孙数不清的恩惠,也带来了无数的痛苦。

更重要的是,频繁发生的洪灾每次对于宁厂来说,都算是毁灭性损坏,冲走了财物,冲走了生命,更冲走了许许多多关于历史的记忆,留下的只能是无限遐想。
祖祖辈辈积累的坛坛罐罐,诗书典故,历史记忆,一河洪水,就付诸东流。
另外一个原因是考古发掘工作的滞后。由于整个三峡地区考古工作起步较晚,同时为了配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需要,几十年来各级考古部门的发掘重点一直集中在海拔175米以下的淹没区,“巫山人猿”化石的发掘,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。巫溪境内为非淹没区,考古发掘工作进展缓慢。
地下掩埋了太多的秘密,地下有太多的未知。留给研究者的,只能是合理的推测与想象。
被掩埋着,就有被掩埋的理由。
未知,只能在合理的时候才会显现。
从巫山山脉到大巴山山脉,再到武陵山山脉,广袤的土地下,被掩埋的是无尽的秘密。
地上,是众多如宁厂古镇一样已经破落,濒临绝迹或已经绝迹的古代文明,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村寨、摆手堂、风雨桥、宗祠、庙宇、土司王城等建筑遗址,是汉、土家、侗、苗、白、羌、傣、布衣等众多民族之间共同依存的文化现象。
地下,还有数不清的未知。
地上地下,铺就的文明长廊,盐味厚重。
研究这些文明,就是研究中华起源文明。
话题太厚重,一说又需万语千言。
还是回到宁厂。
宁厂,看透一切,无需被证明,无需被拔高。
历尽沧桑,依旧平淡。
听风,听水,听晴,听雨,听四季更替。
看喜,看悲,看古,看今,看世事无常。
山,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。
水,流了又来,来了又流。
唯宁厂,以自己的姿态,站着。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作者简介:唐文龙,80后,重庆巫溪县人。喜摄影,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、新华社签约摄影师,用色彩和形状表现哀愁与欢乐。喜文,当过农村小学教师,做过党史研究工作,获得过没有记者证的重庆市首届十佳“田坎记者”称号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散文学会常务理事、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,华龙网“鸣家”、重庆晚报“夜雨”专栏作家,重庆市文旅融合专家库成员。发表各类诗歌、散文等文学和新闻作品百多万字,多次在各类征文、摄影比赛中获奖,出版有《小人物讲大道理》,长篇文化散文《巫盐天下》,一直敬畏着文字。喜书,好读书不求甚解,获得过重庆市第七届十佳读书人称号,一直自娱自乐,对镜黄花,临窗醉月。网名“黑蚂蚁”,毫不起眼,柔弱渺小,但始终模仿着蚂蚁的姿态,坚持,坚韧,倔强地爬着,虽然慢了点,但一直向前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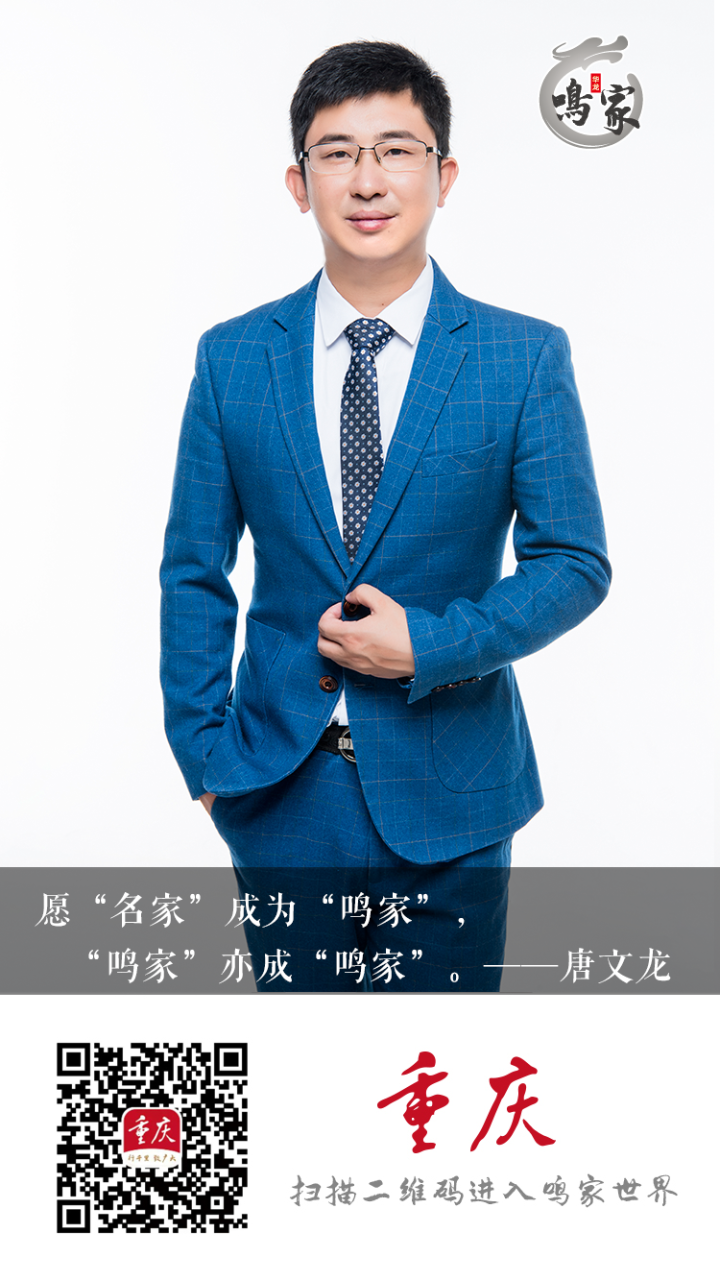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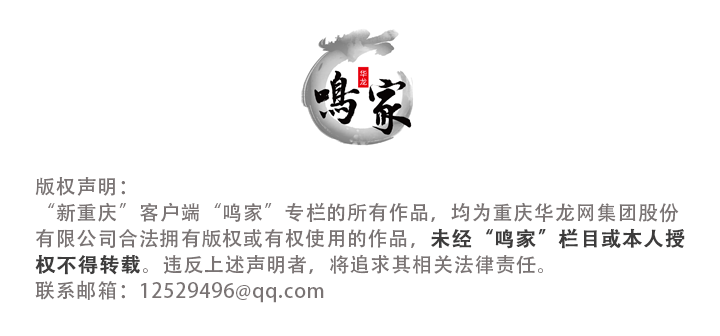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人人重庆
人人重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