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进:必须守住诗歌和诗人的门槛
诗歌的门槛越来越低,每天成百上千首新写的“诗歌”涌出,好像写诗已经成为天下最容易的事。做诗人的门槛也越来越低,随便扔块石头,就可以砸伤好几个“诗人”。同质化的平庸作品四处可见,好诗、大诗却屈指可数。诗坛热闹,诗歌寂寞。

有一种流行理论,据说新诗的“新”就在于它的无限自由。在这些论者那里,新诗似乎就是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些与大众无关的个人体验的“艺术”,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审美标准的任性的“艺术”。
其实,诗的命脉首先就在于接地气。诗人要有入世的热情,就像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说的那样: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”
诗抒发的是艺术情感:经过淘洗、提高的社会情感,而不是原生态的私人情感。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的资格。以自己的独特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,才可能成为时代认可的诗人。孟浩然的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;白居易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;臧克家的“有的人活着,/他已经死了;/有的人死了,/他还活着”.诸如此类的名篇之所以广为流传,就是他们说破的正是大家想说而又没法说出的人生体验。就像《白石诗话》所说:“人所易言,我寡言之;人所难言,我易言之,自不俗。”
翻开诗歌史,优秀诗人几乎都不是只热心守护自己心灵,总有家国情怀,“心事浩茫”。大格局成就大诗人。“心催泪如雨”的李白,“穷年忧黎元”的杜甫, “划呀,划呀,父亲们” 的昌耀,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海子;都是令国人处于呼应状态的姓名。以身许国,准备马革裹尸的辛弃疾,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陆游,不是在用墨,而是在用血和泪铸造词章。
接地气,诗才有强大的生命力;而有贵气,诗才可以提升读者的心灵。
所谓诗的贵气,就是诗人要有出世的智慧。所谓“有第一等襟抱,才有第一等真诗”。对于滚滚红尘,诗人要善于给予诗的观照。敬畏人性的纯净,倾听内心的声音,在世俗世界、功利世界里和读者一起寻找回家的路。诗人的敏感和智慧,给同时代人带来警觉与思考。诗人的悲悯情怀,打动着抚慰着读者的心。
往往在一个大的事件以后,总会迅速地出现一批又一批的诗,而后,这些诗又会像出现时那样迅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,流传下来的只是极少极少的篇章。能够取得生存权利的少数诗歌正是既接地气又有贵气的作品,应景,蹭热点,和真正的诗歌无关。

运用诗家语的能力,这是评判诗人优劣、文野的另一个基本标准。诗不说故事,它是心灵艺术,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言说者。诗的旨趣不在客观世界本来怎么样,而在客观世界在诗人看起来怎么样。化客观为主观,化现实生活为内视生活,这就是诗人的全部工作。不讲故事的诗,也不讲“人话”。在诗的形式美学要素中,诗的语言非常要紧。宋代王安石把诗歌的语言称为“诗家语”,有其道理。诗就是诗,使用回车键并不能把一篇散文变成一首诗。
要从“寻思”走向“寻言”。在限制里寻找张力,在法则里寻找自由,当然是件难事。中国古代诗话记录了许多古人在这方面的逸闻趣事: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根须”,“句句深夜得,心自天外归”,“吟成五字句,用破一生心”。没有这种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追求,哪有辉煌的中国古诗?
诗家语不是一般语言,诗人进入创作状态以后,他就离开了现实世界,“肉眼闭而心眼开”,在心灵世界漫游。诗的本质是“不可说”,它是无言的沉默,无声的心绪,无形的体验,以言来言那无言,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,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。所以诗人往往感叹:“口开则诗亡,口闭则诗存” ,“情到深处,每说不出”。一般语言必须质变才可能成为诗家语。杜运燮写秋天:“连鸽哨都发出成熟的音调”;舒婷写理想:“理想使痛苦光辉”;傅天琳写学生的暑假:“让我们把暑假放得远远的/放到九寨沟去放到草地去”。精炼,别致,情思含量很高,在散文里绝对是遇不到这样的语言的。
诗家语也不是特殊语言。诗人越成熟,他的作品就越平淡。镂金错彩,珠光宝气,华词满篇,扑朔迷离,是写诗幼稚病。“才大于情”绝对不是诗人高明的证明。如宋人苏轼所说:“绚烂之极,归于平淡”;也如另一个宋人葛立方所说:“落其纷华,乃造平淡之境”。
诗家语是一种怎样的语言呢?它是一种言说方式,一种诗人“借用”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。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说方式就发生质变:意义后退,意味走出;交际功能下降,抒情功能上升;成了具有音乐性、弹性、随意性的灵感语言,内视语言。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,就是“精致的讲话”。
不像散文,诗不在连,而在断,断后之连,是时间的清洗。诗在时间上的跳跃,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。
臧克家的《三代》只有六行——
孩子
在土里洗澡;
爸爸
在土里流汗;
爷爷
在土里葬埋。
六个诗行却既写出了一个农民在“土里”的一生,又写出了农民在“土里”的世世代代、祖祖辈辈的命运,从具象到抽象,从确定到不确定,从单纯到弹性,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。
不像散文,诗不在面,而在点,点外之面,是空间的清洗。诗在空间上的跳跃,使诗简约而丰富,以一驭万。余光中的《今生今世》是悼念母亲的歌。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“最忘情的哭声”,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,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。“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/有无穷无尽的笑声”,这“笑声”最多样,最丰富,最漫长,高明的诗人却把它全部“清洗”了。诗之未言,正是诗之欲言。可以说,诗的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。恰是未曾落墨处,烟波浩淼满目前。母子亲情,骨肉柔情,悼唁哀情,全浸透在诗签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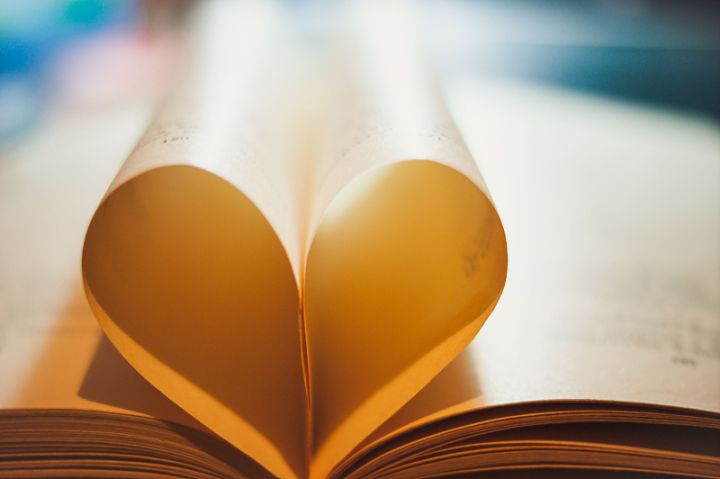
必须从提炼诗情和提炼语言两个向度重建写诗的难度,守住诗歌和诗人的门槛。我以为,这是诗人、诗评家、诗歌编辑面临的刻不容缓的美学使命。
鸣家简介:吕进,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西南大学二级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中国文联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委委员,重庆直辖市第一届文联主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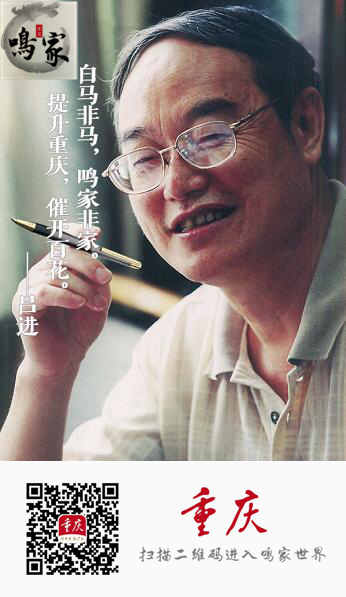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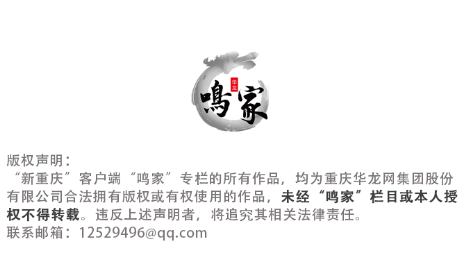


 无障碍
无障碍
 亲爱的用户,“重庆”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“新重庆”客户端。为不影响后续使用,请扫描上方二维码,及时下载新版本。更优质的内容,更便捷的体验,我们在“新重庆”等你!
亲爱的用户,“重庆”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“新重庆”客户端。为不影响后续使用,请扫描上方二维码,及时下载新版本。更优质的内容,更便捷的体验,我们在“新重庆”等你!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