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进: 双城之恋
成都,我的故乡
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正在推进,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。在文化上,巴蜀其实从古及今就是一个整体的区域概念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行政区划的变化,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(重庆)和蜀(四川)截然分开。川菜、川剧、川妹子、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,也属于重庆。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,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。

我是生在成都的蜀人。从位于成都后子门的川西实验小学毕业后,在成都七中就读六年,然后到重庆念大学,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。记得八十年代在北京出席全国教代会的时候,四川代表团团长、四川省副省长韩邦彦曾经在代表团的会议上说:“没有川西实小,没有成都七中,就没有吕进教授。”
川西实小现在是成都实小,校园很大,李鹏、韩邦彦都是川西实小的学长。成都七中是百年名校,它是清华、北大的重要生源基地,每年考进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要占成都招生人数的一半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,学校有4位理科教师颇受欢迎。学生们编了一首顺口溜:“真物理,假化学,熊代数,唱几何”。真物理是指姓曾的物理老师,他毕业于北京大学,后来调到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。假化学是指姓贾的化学老师,在我毕业后他调去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。熊代数非常有个性。1957年秋天,他第一次来上课,我们想,他可能会规范些了吧。结果他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教育局的大人们有毛病”,惹得哄堂大笑。上了熊老师的代数课,不需复习,一切了然于心。唱几何当然是几何老师,他是咏唱着上课,唱到重要地方,会改为说话:“注意,这里很重要啊!”
成都七中文理并重,百年中,文理科都出人才。2005年5月,在成都七中百年校庆的庆典上,校长王志坚致辞:“成都七中百年的历程,培养出了李萌远、陈家镛、叶尚福、王昂生等院士和屈守元、吕进、白敦仁、冯举等知名学者。”这院士之外的四位,都是文科学者。
我的语文老师是白敦仁,明代文学专家,他教的《木兰诗》等古代名篇,我至今也能背诵。有一学期开学,我家太穷,实在缴不出学费。白老师是班主任,我的妈妈找到白老师。家境并不宽裕的白老师立即说:“吕进的学费我缴了,这个孩子不能耽误,他将来必定有出息的。”我读高二时,白老师奉派去波兰华沙大学中文系任教,我曾赠诗《送白老师远行》,最后一节是:“遗憾自己不能长出翅膀/在天海里划着,为你送行/我将一颗爱心付与一弯明月/送老师到密兹凯维奇的国境。”白老师后来调往成都大学,出任中文系系主任。成都七中还有一位好校长解子光,他在成都七中任校长26年,后来任成都市教育局长。他做报告极受欢迎,以致闹出有学生尿急而又不愿离开会场最后尿了裤子的笑话。成都就是这样一座生我养我的城市。
大学毕业那天晚上,外语系毕业生开会,由系主任赵维藩教授宣读分配决定。白发苍苍的赵主任是山西文水人,刘胡兰的同乡。他用山西腔第一个就宣布到我的分配:“吕进,四川省高教局。”喜从天降,我这个成都人简直高兴得要死:这下可回老家了。回到学生宿舍,却看见门上有人留下的用粉笔写的字:“吕进,明天早上8点在44中门前集合,出去联系学生的教学实习,时间一个星期。”我很纳闷,我不是要回成都了吗。仔细看分配通知书,发现在“四川省高教局”下面有一个括号:西师报到。西师当时还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,是省管,哎呀,高兴了半天,还是留在这里呀。从那一刻起,我就变成了半个重庆人,接受着蜀文化和巴文化的双重熏陶。我的妻子是重庆“土著”,在重庆巴蜀中学毕业后,考入清华大学。因为我的关系,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重庆,我们携手观赏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风景,这是“双城之恋”的又一种解读吧。
巴山连接蜀水
“中国文化一源论”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: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。但是,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,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,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。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,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,但是长江流域(尤其是巴蜀地区)、珠江流域、燕辽地区、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。
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区域文化,很自然,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,具有同质性。最相似的就是,不管四川还是重庆,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,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。我在讲学中总是开玩笑说:“巴蜀文化都不是东西。”
巴蜀文化自古以来是建立在“山高皇帝远”的蛮夷之地的文化。地处偏远,和文化权威、文化新潮就若即若离,较少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”,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;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,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,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。东部文化的前沿性、时尚性,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,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。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,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市场总是有限,寿命总是短暂。西部文化的边缘性,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,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。巴蜀文化对于外地、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,并不排斥和歧视。相反,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“希奇”东西,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。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,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:稳健的先锋,或者,先锋的稳健。川菜,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,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,不断推出新派川菜;方言,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,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;川剧在融汇高腔、昆曲、胡琴、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,但又不停地在唱腔、舞美、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。
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,我在外语系俄语专业执教,发生了一场争论。一位广东女生穿了一条西南师范学院从来没人见过的喇叭裤。一些学生认为,这是奇装异服,大学生不适合穿。另一些学生说,这有啥呀,不习惯的东西慢慢就会习惯的。他们争执不下,就到我家里,要听我的看法。我就开玩笑地说,鲁迅曾经说,一些中国人对于传进来的外国东西一味看不惯,一味反对。到了实在反对不了的时候,就改口说,这种东西中国其实古已有之。从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看,有些穿裤子的飞天,那裤子就像现在的喇叭裤。“看来,中国古已有之呀!”学生大笑,一场争论就在承认新鲜事物的氛围里化解了。

巴出将 蜀出相
在文化上,四川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,甚至根本划不开,就像人们说的那样:川渝一家。但是细细观察,也有区别。在饮食文化上,川渝都喜欢麻辣,其实川更喜欢麻,而渝更喜欢辣;川爱好喝花茶,渝流行喝沱茶。在语言上,川渝都属西南官话,其实四川话更软,语句更长,女孩说话更嗲。重庆话更硬,语句更短,更直接。有些词语也不同,比如,四川话说“加油”,重庆话说“雄起”;四川话说“不客气”,重庆话说“不存在”;四川话说“丢人现眼”,重庆话说“脏班子”;等等。
《华阳国志》说:“巴出将,蜀出相”,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。
四川和重庆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,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。但是,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,柔的品格;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,刚的品格。《山海经》说:“西南有巴国”,重庆在远古是巴国。巴国多为穷山恶水,陡山险川。爬坡上坎,逢山开洞,遇江架桥,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、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。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,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,所以巴人性格火爆,重群体讲义气,耿直“干躁”。巴地民风彪悍,巴军能征善战。周伐殷,以巴人为冲锋之兵;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;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;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,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。巴人之善战,被羌人号为“神兵”。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,连号称“上帝之鞭”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。渝籍诗人赵晓梦就有一部长诗《钓鱼城》,吟咏这“上帝折鞭处”,吉狄马加和我都为诗集写了序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巴出将”就不奇怪了。巴蔓子、甘宁、秦良玉、刘伯承、聂荣臻等等都是一代名将。
和重庆相比,四川是一个大平原。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。巴靠山,蜀靠水,蜀的肇始、发展,与治水有密切关系,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。古蜀不仅有以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,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: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、是世界雕板印刷术、世界纸币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。
衣食无忧,文风兴盛,“蜀出相”就是自然的事情了,富庶的生活养成了休闲、安逸、绵软的风气。蜀地多出文人雅士,在文学上,司马相如、陈子昂、李白、杨慎、苏东坡、郭沫若、巴金都青史留名。
文明求同,文化存异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,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,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。当今时代,地区的现代化正在吞食地区的个性化,但是相似性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的多样性、多彩性、多元性的向往。所以,成都文的、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、刚的文化品格,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、在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宏图里,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。
鸣家简介:吕进,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西南大学二级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中国文联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委委员,重庆直辖市第一届文联主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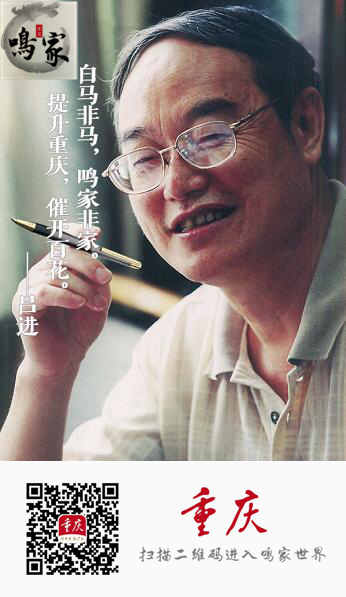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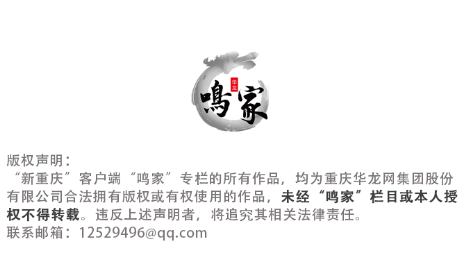


 无障碍
无障碍
 亲爱的用户,“重庆”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“新重庆”客户端。为不影响后续使用,请扫描上方二维码,及时下载新版本。更优质的内容,更便捷的体验,我们在“新重庆”等你!
亲爱的用户,“重庆”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“新重庆”客户端。为不影响后续使用,请扫描上方二维码,及时下载新版本。更优质的内容,更便捷的体验,我们在“新重庆”等你!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