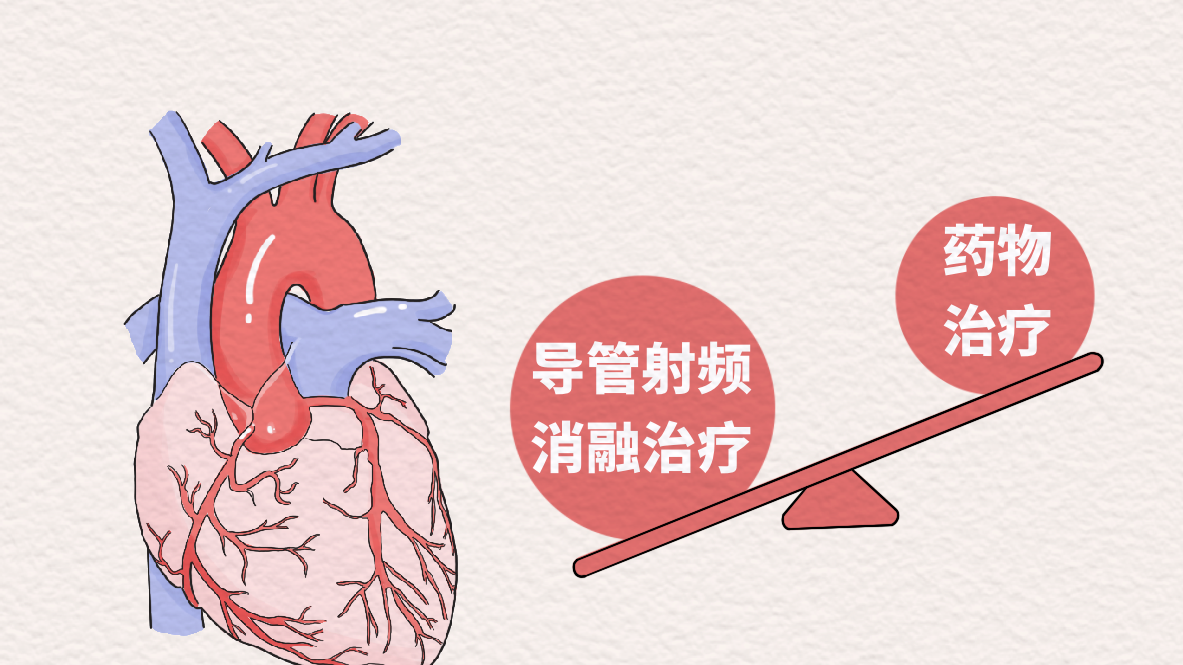王明凯:圆滚滚的西瓜

粗粗壮壮的腿杆,直杠杠往地头一叉:头上是火辣辣的烈日,胯下是圆滚滚的西瓜,弯腰捧起来,抹了泥沙,搁在石头上,一拳下去,咔嚓嚓——脆生生裂成四块,薄薄的皮、厚厚的瓤、黑黑的籽、红红的汁。尝一口,似甘露,像蜜糖,香在口里,甜在心里。
“哦哦,熟啦——熟啦——”木根一蹦弹起来,欢呼着,奔跑着,欣喜若狂,拳头在空中挥舞,身子像要飞起来一般。能不高兴吗?恁大匹坡,遍地是瓜,黑的、白的、圆的、长的,像神仙降下的圣果,静静地躺着,比山上的石头还多。
不容易呀,辛勤的耕耘,拼命的劳作,从冬天到春天,从春天到夏天,从夏天到现在,翻地、点籽、除草、施肥……手上磨起多少层茧?身上掉了多少层皮?
好冷的风呵,刺裂了手,刺裂了脸,刺得骨头钻心痛。他倦着身子不停地拔呀、拔呀,日出、日落……拔光了坡上的茅草,他迎着寒风不停地刨呀、刨呀,一天、两天……刨净了地里的石头。终于,狗都不屙屎的荒坡瘠壤,在他手上变了容颜,松软的泥土里冒出了西瓜的嫩芽,勾着头,躬着身,像托起水灵灵的问号……
好热的天啊,赤日炎炎似火烧,一把汗水甩八瓣。他脚上踏着草鞋,胯上挂着裤衩,光溜溜的肩膀,肩着光溜溜的扁担,一挑挑水、一挑挑粪,从山脚挑到山上,大瓢大瓢地倒进瓜窝子里。好高的坡、好徒的路,一步、两步……一挑、两挑……爬呀、爬呀,口干舌燥,七窍生烟,汗水浸湿了坡上的土。淋呀、淋呀,淋得瓜苗牵了藤,淋得藤上开了花,淋得瓜花结了果……
好长的夜呀,像他肩上的扁担,一头挑着月亮,一头挑着太阳。从西瓜有碗口大的时候起,他就夜夜守瓜,一防野物啃、二防强盗偷。一把凉椅、一把蒲扇,陪伴着他,看月亮走路,看星星眨眼,听夜鸯歌唱,听山蛙鼓鸣。渴了,咕咚咚喝两捧凉水;饿了,干渣渣嚼两碗包谷粑粑。刮风下雨,蚊叮虫咬,一夜、两夜……
终于,熟了,熟了!香甜的瓜,金色的秋,还有甜蜜的爱……
起风了,山风从垭口上吹过来,青枝礼拂,竹叶沙沙。木根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,任风掀动密匝匝的黑发。轻轻的秋风啊,你在诉说什么?是往日的悲辛,还是丰收的喜悦?
十五岁上,木根就殒了爹娘,哭肿了眼,流干了泪,挂条刷把裤儿,连夜走出了生他养他的木家,去过那要一顿吃一顿,饱一餐饿一餐的寒酸日子。身处异乡,茕茕孑立,走到哪里黑,就在哪里歇。
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木根,打喷嚏都没了气力。走投无路,便产生了一个念头:偷。多么可怕、多么羞辱的字眼,是啊,从妈肚子下地以来,还没做过这种事,可是……他爬进了人家的西瓜地。月亮看着他、星星看着他,心里咚咚响,身子像筛糠,像有莫大的不幸等着他。果然,出师未捷身被擒,刚刚摘下一个圆滚的瓜,“咚”的一声响,从坎上跳下一个人来,一把揪住了他。
那是看瓜老人。他喝令木根抱了那瓜,跟他来到一个草棚里。那草棚,几根木棒棒一架,面上搭床凉席,再铺一层麦草,白天遮太阳,晚上遮露气。老人从木根手里接过那瓜,从凉床底下抽出一把杀猪刀,几刀下去,便是几块,殷红殷红的液体直往外淌,“吃吧”他递给木根。
两双眼睛,四目相对。一个惊异、恐惧,一个坦然、温和。“吃吧,在这里是没事的,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”哼,吃就吃,已为砧上肉,只有随它去了,要打要杀,先落个肚儿圆。木根双手抱起瓜就啃,狼吞虎咽,眨眼吃了个一干二净。老人又从棚外抱来两个西瓜,用刀切了,木根又吃。肚子里有了底货,才慢慢尝出了瓜的味道,呵,真甜……
“突突突突……”打断了木根的思路,一辆四轮拖拉机吐着白烟,爬上坡来了。木根一个鲤鱼打挺,抓起一块红浸浸的西瓜,叮叮咚咚,向拖拉机跑去。“熟了,熟了,你尝尝吧,‘阿庆嫂’,哦不不,玉梅。”
“咚——”拖拉机上跳下一个姑娘,团团的脸,圆圆的眼,嘴巴笑成了月亮弯。她叫卢玉梅,是乡农机站出色的拖拉机手,因容貌酷似洪雪飞,且性情开朗,活泼大方,众人便叫她“阿庆嫂”,她也受之乐意,喂喂地答应。久而久之,人们便不再叫她的本名。
“阿庆嫂”下得车来,一瓣瓜就伸到了她的嘴边,她咬了一口,甜津津吞进肚里,瞭一眼满坡翡翠色的瓜地,明知故问:
“都是?”
“都是。”
“熟了?”
“熟了。”
“好,收瓜!”一声令下,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。她帮他摘瓜,一个、两个……眨眼就是一筐。他自己挑瓜,一挑、两挑……眨眼就是一堆。太阳在头上烤着,脚下的砂子滚烫滚烫,出汗了,汗水从额头、鬓角冒出来,带着咸味、涩味、苦味,浸进眼圈、嘴角,他全然不顾,挑着担子,脚快如飞,“叽咕叽咕噗噗噗……叽咕叽咕噗噗噗……”叽咕叽咕——是担子在肩上唱歌,噗噗噗——是双脚有节奏的踏动,深沉、凝重、和谐,构成一种肃穆与欢悦。衣服湿透了,裤子湿透了……
大汗淋漓的木根,望着满当当一车瓜出神,那就是血汗,那就是收获!“啪——”肩上突然吃了一巴掌,“咯咯咯咯……”一串银铃响着,递过来一条毛巾,他擦了把汗,望着她那对美丽的酒窝,领会她那双大眼溢出来的笑。
“等着吧,不到一个小时,就给你换回一把‘大团结’。”旋即,她跳进驾驶台,探出头,单手一挥,踩响了油门松开了刹,像一团火,像一股风,把一车西瓜“突突突”地卷走了,飘起一串袅袅的白烟。
待那白烟在对面梁上消失了,他才回转神来,伸伸腰,甩甩手,慢慢来到地头,又开始摘瓜、装筐,一挑一挑地挑到公路边堆着。一趟、两趟……公路上堆起了瓜山,他猜想足够装一车了,才一仰身躺下去,拉一个长乎乎的瓜枕在头上,四仰八叉摆伸身子,眯上眼皮,追溯那逝去的往事。
……就是那个晚上,木根吃完三个西瓜,脱下衣服算抵瓜钱,拔腿要走。老人一把拉住,硬给他披在身上,眼眶里转动着亮晶晶的东西:“留下吧,孩子,我吃啥你吃啥,我活得出来,你活得出来。”木根感恩不尽,三个响头磕了,一头扑进老人怀里,伤伤心心地哭起来……
木根在瓜棚里住下来了。老人告诉他,他姓耿,早年丧偶,孤身一人。木根就亲亲贴贴地喊他耿伯。无儿无女的耿伯,身边有了做伴的,心头比吃了西瓜还快活,自然把木根当自己的亲儿子看待,白天教他干活,晚上带他照夜,渴了,划开一个西瓜,木根吃大半,老人吃小半,饿了,端出一碗包谷粑粑,木根吃两坨,老人吃一坨。木根也巴心得很,恰象老人的“尾巴根儿”,跟进跟出,跟上跟下,划燃火柴给耿伯点烟,轻脚轻手给耿伯搔痒。夜里,一老一少吃饱了包谷粑粑、红苕坨坨,多是一阵嘻哈打笑,木根就搂着老人的脖子要他教歌。不知老人从哪里学来的歌,那曲儿全变了调儿,比他手中的包谷粑粑还黄,那词儿也早改得不成样子,全不是那家人了。木根不管,只顾尖起耳朵听,憋起喉咙学,翻过来,倒过去,唱得溜溜熟。那令人谛笑皆非的歌声就伴着他们寡淡的生活。
秋天过去了,春天过来了,夏天过去了,黄皮寡瘦的木根硬被耿伯的西瓜瓤瓤、红苕坨坨、包谷粑粑喂成了五大三粗的小伙子,一身疙瘩肉,一副牛气力。
模模糊糊,木根睡着了。晃晃觉得,一个软绵绵的东西蒙住的他的眼睛,睁开眼皮,见是一双玉手正钳着他的鼻尖。“阿庆嫂”不知什么时候盘腿坐在他的身边,驱走了他的梦。见木根醒来,她咧开嘴笑了,送来一片撩人的深情,接着,食指点着他的额头骂他“瞌睡虫”,话未吐完,就是一个沁人肺腑的吻,“咯咯咯”地笑着跑了。术根弹起身子要去还礼,像要扯住一块飘飞的彩云。“阿庆嫂”一步跳上拖拉机,正色道:“别闹了,装车!”
于是,他在下,她在上,一个抛,一个接,圆滚滚的西瓜在空中划开了抛物线。一个、两个……西瓜起舞,笑声伴乐,地上的“山”渐渐变小,车上的“山”渐渐增高。一刻,一车西瓜就装得堆尖堆尖。“阿庆嫂”钻进驾驶台,丢给木根一个醉人的笑,“突突突……”又卷走了一团白烟……就这样,一串笑声一车瓜,一车西瓜一串笑。
“突突突突……”“阿庆嫂”从东镇回来。
“突突突突……”“阿庆嫂”从西镇回来。
“突突突突……”“阿庆嫂”从南镇回来。
“突突突突……”“阿庆嫂”从北镇回来。
……跑了多少趟,拉了多少车,他已数不清了,只是一个劲地摘瓜、装车、装车、摘瓜,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他干得太猛了,脚耙手软,腰酸背痛,肩膀在扁担下压出了一砣一砣的死肉,脚杆在茅草上划出了一道一道的血口子。能歇歇吗?不能,熟透了的西瓜、突突突的响声,催他一个劲干呀、干呀。他好象看见“阿庆嫂”丰腴的手飞快地点着“大团结”,哗哗哗——一百……哗哗哗——两百……哗哗哗——三百……对了,国庆节结婚的时候,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他的新娘子,料子裤儿、翻领罩衣、棕色皮鞋……
瓜收完了,人也瘦了,四肢无力,像散了骨头一般。“阿庆嫂”来了,脚没进门,先是一串咯咯咯的信息。她提来一篮鸡蛋,要木根每天早上吞下两个,好好补补身子。接着,将卖西瓜的存单点给了木根:
“初七,一千一。”
“初八,一千二。”
“初九,一千三。”
……
天哪,整整一万三千元!木根傻了眼,张着惊奇的嘴合不扰来……发财了么?发财了么?他哭了,仿佛手中捏着的不是存款单,而是一眼涌不尽的泉。
那天早上,木根醒来,见身边没了耿伯,心里感到不安。半月前,木根得了一场重病,内吃药,外打针,几天就把耿伯的钱包抠了个底朝天。别无它法,耿伯就天天顶着月亮出门,到大山里挖草药,内服外敷,总算拣了条命。大病初愈,十分虚弱,耿伯几次要摘挑西瓜卖了给木根抓药,只是木根不答应。队上的瓜,敢吗?事情穿了,还不背个强盗皮皮?
木根起了床,到梁子上呼吸新鲜空气,看袅袅炊烟升腾,心里想着老人的恩泽,嘴里不由得唱起了歌……天边来了风,吹来了黑沉沉的云,泼下一阵暴雨。木根回到瓜棚,里面己坐着一高一矮两个陌生人。
“你小子,歌唱得不错呀。”高个子向着木根说。
“嘿嘿,不行。”
“跟谁学的?”
“耿伯教的呗。”
“再唱一遍咱们听听。”
木根唱了,词儿才吐一半,就“啪啪”吃了两耳光,接着是对方阴阳怪气的狞笑:“乱改歌词,捆起再说。”木根还没醒过神来,就被反剪了手,绑在瓜棚外的桐子树上被雨淋着,两个家伙动手捣毁瓜棚。木根义愤慎膺,厉声质问:“你们,凭什么……”
矮胖子一挥筋暴暴的拳头:“嘿嘿,就凭这个。”
“等耿伯回来,要找你们算账的。”
“哈哈,别做梦了,你那干老汉低头认罪了。”
“他有什么罪?”
“你小子不是比我们更清楚吗?盗窃集体西瓜。”
“胡说!”木根怒目圆睁,破口大骂,换来的是一阵拳打脚踢,他觉得一股热血上涌,头昏目眩,身子象只进了水的破轮船,一个劲儿地往下沉、沉、沉……
醒转过来,已是晚饭时分。睁开眼睛:黑漆漆的板壁、黑漆漆的檀檩条、黑漆漆的瓦沟……接着,是一双慈祥的目光。呵,他躺在耿伯久未卧宿的那间小屋里。耿伯扶着他撑起身子,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:“唉,总算退烧了,整整睡了一天啊。这些填炮眼的,一个病坨坨,哪经得起收拾?木根哪,吃药吧。”老人把药水喂进了木根嘴里。
木根紧紧拉着老人的手,泪珠在眼角闪动:“耿伯,你……吃苦了。”
“没什么,”耿伯看似若无其事,“黄泥巴脚杆,只怕饿肚子,不怕戴帽子。”说罢,又端来热气腾腾的鸡汤,“喝吧,要不是在场上我眼快手快,把两张票子塞进鞋底板里,只怕这药汤和鸡汤……
木根接过碗,疲惫的目光凝视着老人手肘上紫一块青一块的肌肤,他一阵心悸,看见了双双拳头向老人挥动,一只只穿着塑料凉鞋的大脚照老人踢蹬……再也忍禁不住,噙在眼角的泪珠滚了出来,涮涮涮地落进手中的鸡汤里……
是呵,拼死拼活地干,风风火火地忙,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应有的报偿。忙完了整整一个年头,总算落下了几天空闲。可是,捏惯了锄把的手空不得,压惯了担子的肩歇不得,心里空落落的,站坐都不自在,总像欠缺什么。木根斜在床上,浏览着眼前的家什:铁壳水瓶上那只小花猫一点也不可爱了,往日的笑脸变成了凶像,张牙舞爪扑过来,像要吞食一只待毙的老鼠。墙上那位美人一扫往日的妩媚,目光冷峻得叫人惧怕,像要透视你的五腑六脏。高柜镜片里的小伙子,愁眉苦脸,郁郁闷闷,似有无限的惆怅又无可言状……他下意识闭上眼睛,更觉头昏脑胀,周身都不舒服。真是人一闷,生百病啰。
“耿伯,还是让我走吧。”木根看着清瘦的老人,痛惜着自己一墩疙瘩肉,有力无处使。瓜棚毁了,饭碗也就被轮起了,再留在这里,不知还要给老人增添多少麻烦和贫困啊。
耿伯把一挑蔑丝炭兜和一根青扁担交到木根手里:“这就是饭碗,有了它,就饿不死人……”
从此,木根肩上压上了沉甸甸的煤担子,天不亮上山,半下午回村,出门一挑空担,进屋一挑煤炭,从东头到西头,挨家挨户送货上门,不图活路钱,只要肚儿圆。晚上,就与耿伯厮守在一起,听“张飞杀岳飞”、“周瑜打黄盖”,倒也乐在其中。
这村子刚好十五户人家,户户姓耿。木根挨家挨户送一担煤,咬三顿冒儿头。一圈完毕就是半月,转上二十四周,就挨边过年了。年关前夕,木根就挑夹码担子,给每家人多送一挑煤。村上的人重感情,他们免除了二十里外挑煤的苦力,忘不了木根的好处,每遇逢年过节,就要排着轮子拉耿伯和木根吃饭,待如贵宾。
……转眼,历史篇章上留下了闪光的记号:农村搞起了责任制。耿伯劝木根:“回家包份田地吧。”可木根不愿意,耿伯老了,一年一年梭下坡,能甩掉他自奔前程吗?老人劝慰他说;“不要紧的,就听大伯一句话,回去吧?只要你挣出个样子,把婆娘讨进门,大伯就心满了……”
就这样,木根回到了木家。田土已划下去了,只剩下那一坡无人承包的荒地。木根二话没说,接了过来,种粮食不行,就不能种经济作物吗?木根首先想到的是西瓜,抱着侥幸心理,在坡上挖了两百个坑点上瓜种,到秋天,摆下了一地翡翠色的“地雷”。第二年,大起胆子,遍坡点上瓜种,然后,便是西瓜丰收,无尽的忙碌、满心的喜悦。
可眼下……木根认定自己病了,什么病,不知道。说不出哪里痛哪里痒,只觉得心里烦躁,嘴里苦涩,脑壳沉甸甸的,像戴了紧箍咒。也许是苦的,累的,找医生看看吧,他这样想。可是,那起什么作用?那些医生,问病拿药,能看出这种症候?病,在头上还是脚上,在肝脏还是心脏,自己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,医生能诊查出来?
对了,国庆节——婚期步步逼近,可自己这副样子……“阿庆嫂”带信来说,明天就到公社办手续,顺便把拖拉机开进城逛两天,立柜平柜那些,该买的买了,顺脚拉回来,不就都妥贴了,可这……
一个月前,耿伯托人打信来说,他一切都很好,可那地方还是那个字:穷。村上的人只是填饱了肚子,与富字还没沾边。上山担煤炭,上街买化肥,爬坡上坎,还是靠一副肩膀两只脚。那么出西瓜的土,却没人种瓜卖,七弯八拐,爬十里坡路才能望见公路,瓜熟了,你靠两只脚担出山?一句话,交通条件限制了他们致富的路。好不容易从别村接通一条机耕道,一拢村头,又让响水河给拦住了,要治服它,得花一万块钱修座拱桥……木根重把那封信找出来,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,心里泛起深深的内疚和浓烈的不安,离开耿伯两年了,也从没回去看看,他还亮着那黄牛嗓子唱歌吗?他还把叶子烟杆吸吮得嗤嗤地响吗?那阵,一条铺盖里裹两条光棍,心与心贴在一起。可现在,却隔得这么远,山高路遥,靠鸿雁传递相思,呵,那深沉的情愫啊。
蝉声听不见了,蛙声听不见了……朦艨胧胧的世界,飘着朦艨胧胧的雨,一个黑点,由小变大,在雨里蠕动、蠕动……哦,那是一位老人,挑着沉重的担子拾级而上,多么沉重,多么吃力,他的背压成了一道没有弦的弓……看清楚了,那正是耿伯,那正是两年前压在自己身上那根青杠扁担和那挑蔑丝炭兜……他追上去,追上去,执意要接过老人的担子,老人却推开了他,竞自走了,越走越远,越走越远,他焦急地大喊起来:等着我——等着我——
一个冷颤,他醒了。想着刚才的梦,再也无法成眠,想呀、想呀……鸡叫了……天亮了……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来了……“好,就这样!”一个跳跃下了床。他觉得自己象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,找到了克敌出胜的妙法!
水顾不及烧,饭顾不及煮,胡乱麻了帕冷水脸,急冲冲出了家门。他要去见“阿庆嫂”,去见他心上的人……他一切都想好了,他要告诉她:第一,把她的拖拉机开到南山,他要去看看那是的山,那里的水,看看昔日架瓜棚的坡上还是否存有他的脚印;第二,他要拿出一万块钱,借给那里的乡亲们,让他们早日在响水河上架一道虹,送走贫困和忧愁,把富字牵进山窝;第三,他要作耿伯的儿子,把老人接过来,和自己住在一起。这三条缺一不可,他想,她一定会答应的。不然,就不忙跟她扯结婚证!
秋风吹得竹叶沙沙作响,绿荫里,一对雀儿在偷笑。他高兴了,拾砣泥丸掷过去,它们扑闪着翅膀,“羞——羞——”地叫着飞开了。木根极目望去,一弯弯田畴的尽处,是一幅多层次的图画,田的紫红、水的深绿、山的青黛、云的洁白……多么使人心旷神怡呀,他真想登上高处,放开噪子歌唱。他感到浑身是劲,头也不痛了,心也不闷了,那莫名其妙的毛病,已经好了一大半……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作者简介:王明凯,作家,诗人,重庆作协原党组书记,副主席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新华文摘》等数十家刊物发表作品数百篇。著有散文集《跋涉的力度》、诗集《蚁行的温度》《巴渝行吟》、短篇小说集《陈谷子烂芝麻》、文艺评论集《让谶言放射光芒》、文化专著《城市群众文化导论》、长篇小说《不能没有你》等书籍。曾获文化部群星奖、全国新故事创作一等奖、中国当代诗歌奖、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、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、重庆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奖项。




 无障碍
无障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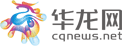
 亲爱的用户,“重庆”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“新重庆”客户端。为不影响后续使用,请扫描上方二维码,及时下载新版本。更优质的内容,更便捷的体验,我们在“新重庆”等你!
亲爱的用户,“重庆”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“新重庆”客户端。为不影响后续使用,请扫描上方二维码,及时下载新版本。更优质的内容,更便捷的体验,我们在“新重庆”等你!